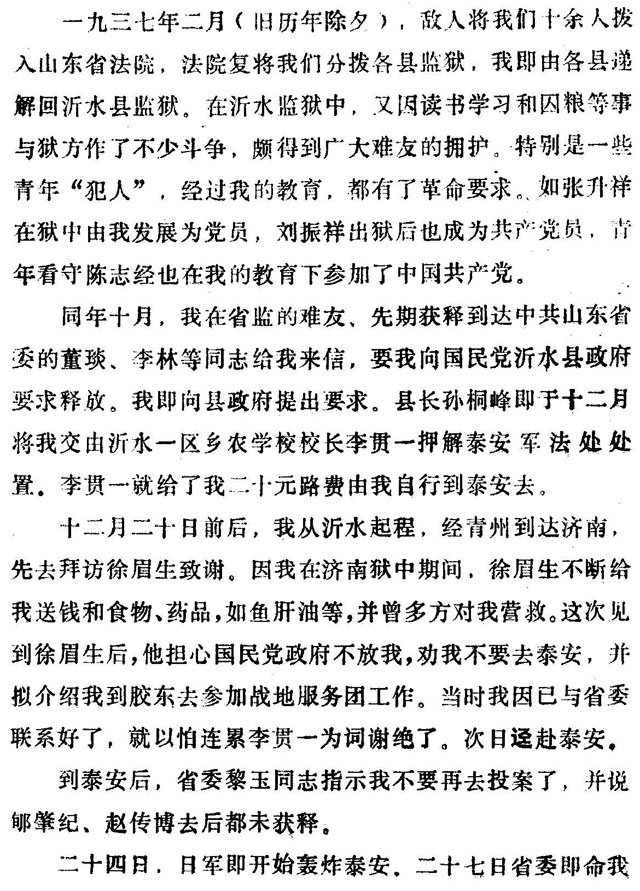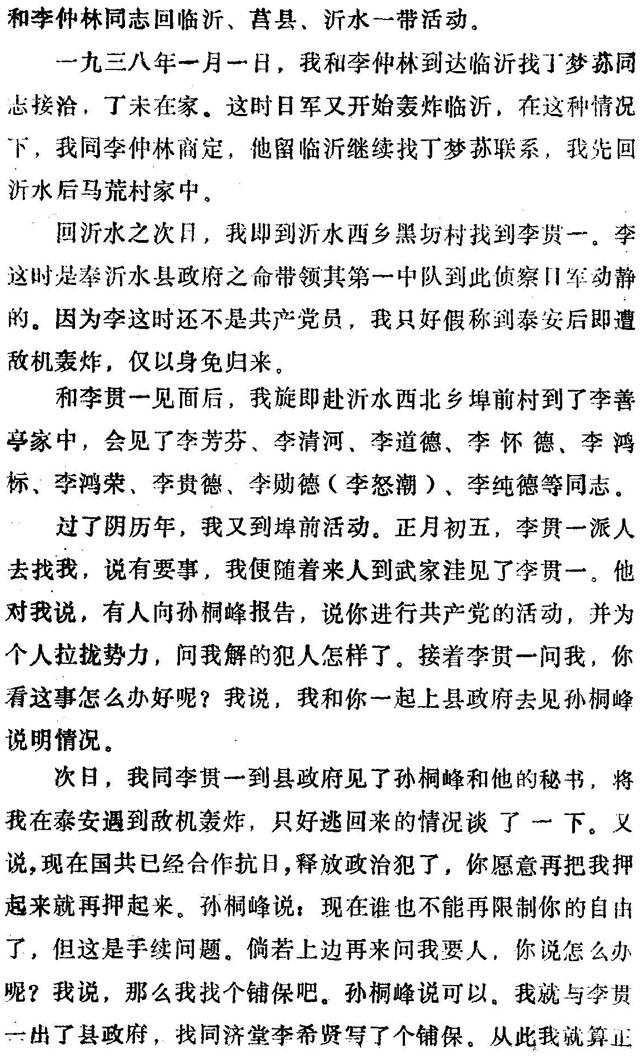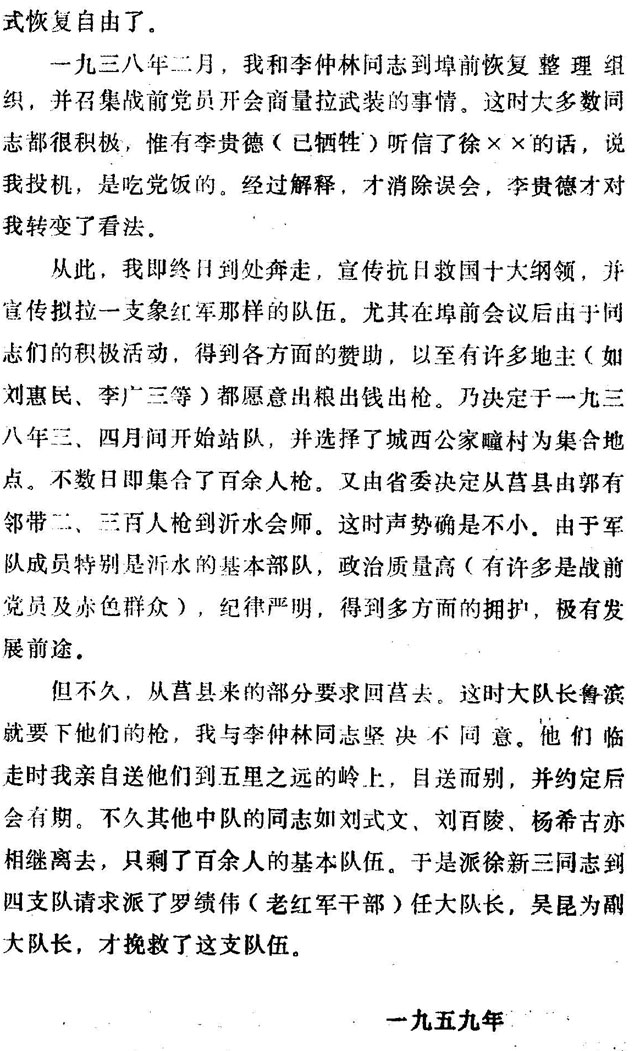邵德孚自传 (节录)
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十八日的黎明,我在校(已放暑假,我仍在校)尚未起床,忽有数人到我寝室叫醒我,说:因吴光城发生误会,要我去县府解释。我当时对去的人均不认识。他们催我正‘急,在我去厕所时,发现他们监视着我,我已意识到有问题。这时已想不出好办法,乃以交代学校钤记与个人手章为名,去暗与刘瑞徵(当时任教务主任,同情分子,一九三八年参加四支队六大队,改名刘浩,系张寅初之爱人,现在青岛休养)同志说:我被捕了,我走后请你将我那里仔细检查一下,看有无文件,及时销毁(后来在她去看守所看我时,我又想起一处存的文件也托刘转告党员学生找去销毁了)。我随他们到县府时,已有五人在,即韩文卿(口口口口口口口口),孙华亭(在济南邮局患半身不遂,已哑,不能说话,现住×东街邮局职工舍宿)于松泉(现在济南市委(府)招待所)、曹泽生(口口口口口口,抗战期间曾任汉奸乡区公所文书,四八年南逃到泰州,解放后在泰州土产公司当传达,肃反后不知怎样了)、刘秩吾(现在沂水任小学教员)。在沂水押了一个时期,即解往济南。在沂水被捕时,当晚过堂即审讯了。韩文卿(受刑)、孙华亭(受刑)均未供认。刘秩吾供出了尹平符是互济会员(当时不知道,以后解决尹平符党籍问题时才知道尹现在人民出版社任副编辑),于松泉(也未承认),因时间关系,我和曹泽生未过堂。次日,宋鸣时找我和曹泽生谈话,宋无耻地说:“我打入你们的组织已久,你们的情况我已全部了解了,共产主义是不适于中国的国情的,现在蒋委员长宽大为怀,只有’自首之一途,自首后给你们生活费,每月二十元,将来有功还可以增加。如果自首,我以人格作保,保证你们生命的安全,否则是没有前途的。……”我当即问他,什么是自首呢?宋说:就是你把介绍谁入党,怎样和他谈的话等说出来……。我说,我不是党员,我如何能介绍别人入党呢?宋说:我还不知道你吗?你是分区书记。我也说:你还不知道吗?我怎么成了分区书记呢? (原来宋在开扩大会议时曾说要我担任分区书记)我不是党员怎么说我是党员呢?静默了几分钟,宋又欺骗我说:这么着吧,你就是不是党员,你可证明他们都是党员。我说:我不是党员,怎么知道他们是党员呢?那不是胡说八道吗?停了一会,宋说你好上考虑考虑,三点钟后同答我。我即回了看守所。也未问曹泽生的话。下午三点钟,问我考虑的怎样了。这时我就给宋写了个信说:我自参加革命以来,未作过任何违犯人民利益的事情,我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,我从来未参加过任何其他政治组织,我并以生命保证曹泽生也未参加过其他组织。以后,宋再未找我谈话,亦未过堂,押了约四十天左右,即解赴济南市公安局军法处。
在宋和我谈话回来后,韩文卿等问我谈的什么:我即告诉他们谈话内容及经过。韩问我是否可以找宋谈一下,我说不要去。韩问我有什么坏处,我说至少没好处。但韩却偷偷地主动地去找来自首了。据了解不但沂水组织情况全讲了,并且承认杀郑耀庭是县委的决议。我知道后即找韩谈话,我说:共产党的官司还不够你打的吗,你还涉及杀人问题?经我分析,韩似乎有些害怕,但我动员他必要时牺牲自己以灭口(以前因老马怕受不住刑曾用过此法)他不同意。以后到济南才翻了供,因系刑讯故未依此判刑。这一问题检查起来,我不应该告诉他与宋鸣时谈话的情形,以引起动摇叛变。固然应由他本人负责,但却表现了我的幼稚无知。
在沂水看守所月余,即解往济南押军法处。黑屋子内四面均无窗,只有一月牙门。这时虽然表面上对别人进行安慰教育,但自己内心里则有些怕死。有三两天的时问过了一堂,就转到高等法院。(这一段可由于松泉证明。)
到高等法院看守所后,曾在法庭上与吴祝村对质。当时法官问:吴祝村,邵德孚是否是共产党员?吴祝村说是。法官问:你怎么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呢?吴说,我去的介绍信是共产党写的。我当时听了又气又怕,气的是他叛交,怕的是他吐实。我即说,你那个信是介绍你当教员的,而不是介绍你作共产党的。敌人过来追问与写介绍人的关系,我又说:吴竹存你得凭良心,你在我们学校里,我们对待你并不坏,你怎能因工作而怀恨陷害。我即向法官说:吴竹村曾因工作中犯错误被我批评过,并因能力不够而被辞掉等,因而吴是蓄意陷害……当时法官就说吴是胡说八道,你在省党部说曹泽生是共产党,邵德孚不是,现在又说耶德孚是共产党,曹泽生不是。这时,吴竹村即说:我当时是受刑不过呀l (经法院验明确曾受过刑),我即说:你受刑不过应当说实话,亦不应胡说。吴即说:我实在对不起你,你骂我吧。这是法官即宣布退庭。我自己也根据起诉书写了答辩书,将起诉书上的罪名事实一一驳辩,理由充分。这时敌人内部可能有矛盾,并未认真追究。本来法院准备判处无罪,但省党部张苇村亲笔批示法院,非判罪不可,因此判了五年徒刑,拨第一监狱执行。自被捕至入狱(一九三三年十一月)共历时一百天。
到济南第一看守所后,虽然不久我就病了。但仍能追随着同。志们与敌人进行斗争(此段可由王云生同志证明,现在移民局)o入狱后(居化字号),对同号及一般青年同志如万宝善(现在依南煤矿)、赵来风(现在济南回协)、褚方塘(已牺牲)、刘连登(已牺牲)、刘秩吾(同案的)等,不断进行帮助、教育。本来也想领导斗争,但因无能及无经验,未发动起来。于一九三五年夏(已拨入良字号)已有王敬功同志(即任佐民同志)的领导,因监方打了袁喆生(已牺牲)同志,即暴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对敌斗争, (逐渐发展到全监狱共七百余人,参加斗争的即有五百余人,内政治犯不过二百人)。这时我虽然身体极坏,刚从病监回来不久(敌人说我病重,怕死到监房内,就将我拨入病监,但我不堪病监之虐待,过了一个时间,即又要求拨回监房),眼又病得看不见,但我已抱不怕牺牲之决心,也随同志们坚持了六天的斗争。当时敌人见我已危机,于夜间曾给我打过强心针。乃于次日结束了战斗。复食后又与许多病重的同志拨入病监,二十余天后仅能扶着墙行走。不久,敌人即将我拔回青州监狱,同行者有李佃臣(同情我们也参加了斗争,普通犯,出狱后抗战期间即牺牲)、贵席珍共三人。(这一段可由卢冠舟、现名刘特夫,在青岛市委,刘庆珊、西安市第四军医大学,向明、前山东分局第二书记,向明被捕时的名字叫王中和,董琰、前山东省委副书记兼省委组织部长等人证明)。
当斗争开始之次日,敌人要每个号里去一代表,我们都不去。又想,斗争已经开始了,还未向敌人宣布为什么作战、绝食也不好,于是良子号而由我和刘庆珊、韩维密(已在四O年肃托时,在泰山区被杀害),去见了二科长(姓什么已记不清,可能是姓张)。当时形势很严重,两边很多看守站道子,并放有很多刑具,有鞭子、杖条、棍子等。二科长即首先叫我去问:你们为什么绝食?我即说:因有一难友袁蒿生被打了手拍子,并且下落不明,我们政治犯感觉不但人格受侮辱,而且生命无保障,兔死狐悲。张说:袁喆生未挨打。我说。这是××人(是跑号的犯人,敌人的腿子向我们示威时说的)说的。可以叫出袁喆生来我们看看,如未挨打即无事了。张又说:袁喆生挨打是因他骂我。张说:邵德孚,若是有人骂你你该打他吧。我即说:是否骂你,我不知道,但按法律讲,刑讯是犯法的,即使杀人凶犯,马上'勺强盗,也不能刑讯,我想监狱的法律,不应该违背国家的法律。这时敌人无话说了。略停了一会,张又说:我打袁喆生,因为他是疯子。这时我笑了,我说:科长开玩笑了,如果是疯子,那么他是精神失常的人,就是杀了人亦不能偿命,科长你打疯子更是违法的了。这时敌人忽然把脸一沉说:各人打各人的官司,这事与你无关。这时我还要说话,敌人即将我推走。对刘庆珊和韩维密也不再问话了。 (这事可由刘庆珊,刘特夫证明)。
这次斗争坚持了六天之久,从表面上看是百分之百的胜利,即全部条件都答复了。但在复食后不到一个月,敌人即无耻地将答复的条件全部推翻,除一部分拨到外地监狱外,将全部政治犯关起来了,每隔一间关一人,不使有两人见面。这次斗争是被敌人欺骗了。也证明了敌人的无耻。
一九三五年五六月间,我同贵席珍(党员)、李佃臣到达青州第四监狱。我们三人单独关在另一个号筒的监房里,但不久我们就与其他同志打通了关系,经他们计划指示,即开始了斗争。首先要由我以要求去镣的方式,向监方提出要求,但敌人不但不给我开去镣,反而给我换上了一付二十磅的大镣,于是斗争爆发了。首先由我们三人开始绝食,继而由全体政治犯援助我们,经过四天的斗争,我们胜利了,有部分同志开去镣,而且我们也与大家合在一起了。在青州监狱一年多的时间,曾进行绝食斗争三,四次之多,每次我都随大家参加斗争,从未动摇或后退。(这段可由田海山、省委党校,邹肇纪、省监委,张晔、前山东分局组织部等同志证明)。
一九三六年秋,由青州监狱送入济南山东反省院。在反省院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,并与其他同志争取团结了大多数政治犯,作“反省制度”的斗争。敌人为了维持其反省摧残,乃以拨回监狱威吓我们,曾先后两批拨回了监狱。我们为了打破敌人的阴谋威胁,乃争取主动,向敌人要求拨回监狱,并绝食三四次以示决心。最后,敌人将我们拨回了监狱。
斗争开始后,敌人曾想瓦解我们,由管理主任王音民(抗战后跟我们抗战而牺牲)找我们谈话,问我们为什么想回监狱。我就说:监狱里好(敌人是最反对说反省不如监狱好),王说:你愿不愿出狱?我说:当然愿意出狱r。王说:你怎么没办法呢?我说:你们不放我,我又不会飞檐走壁,又不会七十二变,有什么办法出狱昵?王说:我给你这个办法,院方让你怎样你就怎样,半年就叫你出院。这时我考虑了一下(我考虑的并不是说他这办法行不行而是考虑如何答复他们),就回答说:不行。王说:你这不是反皮缠吗(调皮的意思)?我说:怎么反皮缠?王说:问你愿否出院,你说愿意出院,问你什么办法,你说没办法,我给你个办法你又说不行,这不是反皮缠吗?我逮时装出很气愤的样子说:我不是共产党,但有人想杀我,就以共产党的名义来杀我,还想要我说杀的对,我死也不干,头可断,血可流,无论如何不能承认说杀的对,我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是共产党员,但我不承认共产党,你们是不放我的。所以别的都行,就是要我承认共产党不行(我们不好说是不履行出狱的手续一一填悔过书,发表反共宣言,只好不承认是共产党这是我们研究的对策)。王说;不但我知道你不是共产党员,徐眉生也证明你不是共产党,但这是手续问题。又说:你哥哥也来信说你家庭生活很困难,你还是想法早日出去的好,你不要被青年们利用你以老卖老。我一听更火了,我说:谁利用我,谁陷害我,我却明白,我的父母均已死了,已经弄得我家破人亡了,有死而已,不必多说。我就回了监房,继续斗争。在这一段,我不但自己坚持了斗争,而且还争取团结了部分同志的斗争。(这一段可由刘庆珊、邹肇纪、董琰等证明)。
一九三七年二月(阳历年除夕),敌人将我们十余人拨入法院转分拨各县监狱。我即被经由各县递解到了沂水县监狱。在沂水县监狱中,又因读书学习及对囚粮等与敌人作了不少斗争(但未绝食)。尤其为了维护多数难友的利益,对青年“犯人”不断进行教育,颇收到广大难友的拥护。不少青年犯人甚至青年看守,如陈志经(党员)、刘振祥(出狱后发展为党员,任排长,在抗战中牺牲),张升祥(党员,后因犯错误消极回家)等都参加了革命。
一九五六年八月写于山东医学院
(未校对谢绝转载)